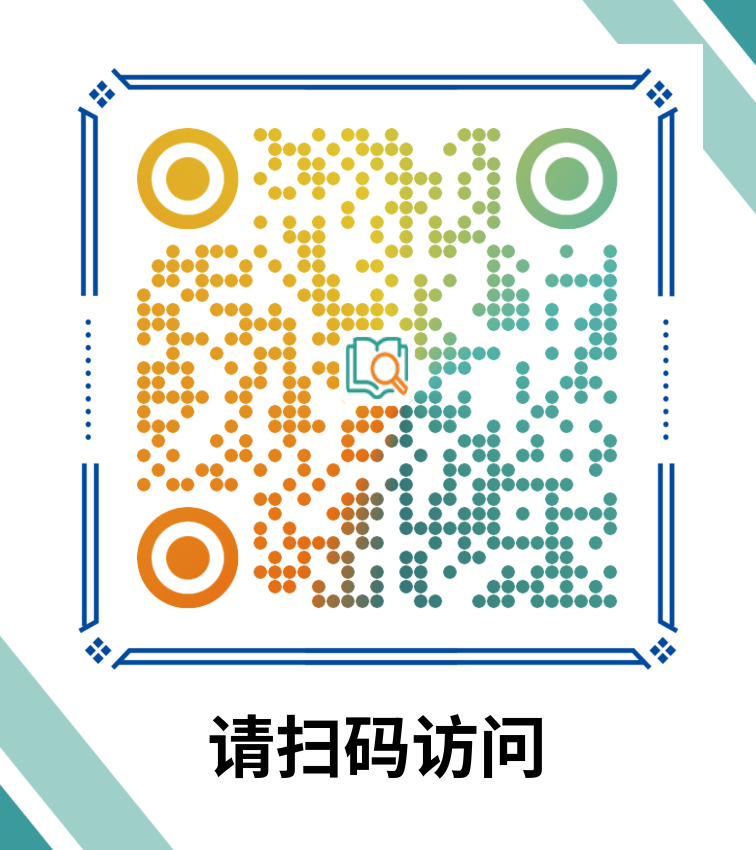2016优秀论据:中式医患关系
时间: 11-04 来源:网络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近年来,医患关系越来越突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呢?
1. 买一本病历,三次受挫
去年我腰痛难忍,好在单位离某三甲医院近,于是趁着午休时间去看。考虑到下午还要上班,我只带了证件、公交卡、银行卡和少量现金。
取完号后准备候诊时,我发现一个问题:忘带病历本了。去挂号处重新排队,排到后工作人员斜斜一指,让我去自动售本机那里买。跑到自动售本机,发现只收一元硬币,而我完全没有。售本机下还有一行提示:如需换硬币,可右转去建档处。
此时是中午12点半左右,我刚刚来到建档处敲敲窗口,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就在那一刹那,建档处的窗帘突然刷地一下拉了下来。再敲几次,里面传来幽幽的声音:午休呢,半小时后再来。
我又尝试去“微笑导医台”换钱,被华丽丽地鄙视了:我们这儿没钱,到别处去。最后,我从一位正掏出钱包挂号的病人那里换到了一块钱,买到了病历本。在窗口碰了三次钉子后,你们说,我对这家医院的印象能好吗?如果在医生那里再碰到什么冷脸(并没有,这家医院的医生护士比窗口部门工作人员态度好百倍),或者医疗中出现纠纷,我会不会也把所有账算到医生身上?用自动售本机卖病历本,或许是个不错的尝试,可以减轻挂号处的工作量,但如果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院方也将本意是便民的服务做得极其不便,并且将各种不便转嫁到病人头上,这算是什么管理思维?
很多时候,病人和家属觉得在医院里处处不便,这不是医生的错,而是与医院的行政管理、建筑设计和基础设施息息相关。
我还有一次郁闷的经历:跑步跑猛了点,脚踝严重扭伤了,一个人去医院看病。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身为残障人士看病是多么不便。骨科在五楼,X光室在地下一楼,挂号划价在这一侧,取药在另一侧,可是走廊两侧没有扶手,洗手间没有残障设施,只能在医院一瘸一拐。事后我在想,医院在改善体验方面可以做多少改进工作?除了像我这样的外伤病人,还有大量不良于行、身体孱弱的老人家,其中不乏无人陪伴的单身老人,为了确保这类病人的安全,院方原本可以在走廊加装扶手,可以以租或借的方式提供轮椅,可以设置无障碍厕所,并加装呼叫铃,以便在发生紧急状况时可以呼救,可以将骨科这类外伤科室在地理位置上离影像检查科室更近一点……然而什么都没有。
我曾前往新加坡北部的邱德拔医院采访,这家公立医院的理念是“hassle free”,即“零麻烦”,医院从建筑设计到管理思维,都以减少病人的困扰和不便为宗旨,比方说可以实时在网上查看每个科室病人的轮候人数,比如有免费巴士穿梭于周边公屋,比如每间诊室上的数字都写得超大,方便年长者识别,比如住院部每个病区主色调颜色不同,以免老人走失。
邱德拔医院走廊有扶手,诊室门上的字号很大,而且颜色各不相同,这都是帮助病人的实际举措。图片来源:网络
由于这家医院所处区域老龄人口集中,糖尿病发作比例较高,在确立了糖尿病专科中心这一重点学科之后,医院管理者又进一步围绕糖尿病相关的健康问题,包括相关的眼科、足专科与护理、康复医学、老年医学科业务……而且最让病人和医疗工作者感到舒心的是,糖尿病专科诊室与老年病科、眼科诊室共处同一楼层,比邻而立,不需要四处奔波。
两相对照,我的结论是:新加坡的公立医院是医院,而中国的公立医院是衙门。大量中国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并非专业医生出身,既不了解病人的需求,也不在乎病人的体验——甚至也不在乎普通医护工作者的需求,病人在求医看病过程中步履维艰,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患者对医生的不满。
2. 医生为什么这么累?
还是亲身经历。两年前,女儿夜里突然捂着耳朵哭闹不止。我初步判断是感冒引起耳道发炎,因为孩子哭得太惊天动地,担心有耳膜穿孔,所以凌晨两点抱着孩子看急诊。
去了某儿童医院后,发现这里简直比白天还热闹。到处是啼哭的孩子和疲惫的家长。我们的就诊很顺利,因为夜间看耳鼻喉科的病儿很少,不过医生的态度让人有点不舒服。这位医生在看诊过程中只问了一句“怎么不好?”检查后说了一声“中耳炎”,再无他话。女儿见面时对她问好,临走时说了声“谢谢阿姨”,也没有得到一句话或者一个微笑。
医生开的药很管用,几毛钱的滴耳液滴了三天后孩子就痊愈了。我一度对医生当时的态度不太满意,但很快我就释怀了,我还记得当天接诊时她的脸色:那是一张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的脸。如果把她当成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会心疼,会劝她好好休息几天甚至辞职。
中国的医患比例已经失衡,而且随着医护人员大量流失,医患比还将进一步恶化。据卫生部2011年统计公报,全国执业(助理)医师246.6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含助理)医师1.82人。在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193个国家中,中国的每千人口执业医生数排名80位。
中国的医生,尤其是大量三级以上医院的医生,每天面对的是庞大的病人数量,需要在门诊、住院、科研、行政等多重任务间奔波。有统计称,在中国,病历书写超过60%的时间;在美国,病历书写时间不超过25%,大量行政事务由医生助理完成。
病人看到挂号的长龙固然会烦躁不已,而医生看到这一幕,简直是欲哭无泪。
病人和家属(比如我)责怪医生不苟言笑,或许不知道这位医生已经连续工作了24甚至36个小时;病人责怪医生出门诊迟到,或许不知道这位医生刚刚做完一台大手术;病人责怪医生5分钟就将自己匆匆打发掉,或许不知道这位医生一上午要看50个病人,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我曾在产检时亲眼看过,妇产医院一位50几岁的主任,一上午看了50个孕妇,一直看到12点多,匆匆吃了三个护士捎来的包子,接着看下午的孕妇。这样的工作强度,我们职场人士也许偶尔有之,可谁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坚持?又有多少人知道医生的加班费、夜班费极其微薄,甚至在今年两会,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看望卫生医药界代表时还需要强调,“医生加班一定要给予加班费”。
换位思考,或许有助于病人加深对医生的理解。我的一位儿科医生朋友跟我说过:当家长深夜抱着孩子来看急诊时,一看前头排着一两百位,肯定会焦虑会烦躁,甚至对医生和医院横加指责;可是换位想一想呢?夜里值班的医生一看到排着一两百个病人,而医生就那么两个,看一夜也看不完,他们不光是焦虑,简直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
3. 医生为什么这么恐慌?
这是一位担任外科医生的朋友的故事,所以在这里使用他的第一人称:
我平常去厕所,喜欢多上几层楼,去老干部门诊,你懂的,那里人少,维护好,比普通门诊干净得多。
有一天啊,我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又赶紧往楼上厕所跑,蹲完后一拉门,就看到一个人站在我面前,看着眼熟,应该是我前两天看过的。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事情是什么感觉,顶多是意外或者纳闷吧。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恐慌,慌得不得了,不知道他会不会从口袋里掏出刀子,然后开始想着该怎么呼救,怎么逃生。我知道这种恐慌完全是非理性的,我自问是个很干净的医生,没拿过回扣没收过红包,跟病人相处得也还算不错,但我在那一刻就是觉得,一定是自己在哪个环节没留神,留下祸根了。
两秒钟后病人才跟我解释说,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有一项特别不好,因为太着急了所以在诊室门口守着我,见我一溜烟儿往楼上跑,就跟上来了。
听完这个笑话,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既辛酸又难过,既为医生,也为病人。
邱德拔医院里张贴着对伤医零容忍的海报。
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等,病人处处疑心,保存证据,不断从亲友或者网络上获取疾病信息,由于“以药养医”等客观现实,他们担心医生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现在还要担心医生是假医生,医院被承包),在首诊后往往还会反复看其他专家,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甚至有可能贻误病情。
医生同样必须步步为营,可做可不做的检查为了保险起见,通通做上,不需要用药的病情无论如何还是要开点药,以免病人怀疑自己看病太草率,这反过来加重了病人甚至整个医保体系的负担。
社会群体之间的互不信任,并不仅见于医生和患者群体。官民、警民、民商、家长与教师,管理者与员工……这是我们脱离了熟人社会的结果,也与法制不健全有莫大关系。从患者角度来说,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各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独立性让人怀疑,患者担心求告无门;从医生角度来说,一旦被患者和家属殴打,甚至被家属强迫向死者遗体磕头,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样相当艰难,如果被鉴定为轻微伤,打人者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往往只被关押七天,难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也与其产生的恶劣社会影响不相称。
4. 最后,让我们回到陈仲伟医生的悲剧上
陈仲伟医生被砍杀事件,至今有众多事实有待厘清:凶手确诊患有精神障碍吗?从芳村精神病院出院时,他的症状是否有所减轻?他的监护人是否尽到了职责?
从现有的少量事实来看,凶手反复纠缠自己的医生,目标明确、反侦察能力高超,不管其行为显得有多么不合逻辑,也依旧是此前医患矛盾的延续,因此这起伤医事件不仅折射出了医者的艰难,社会的戾气,同时还提示出另一个亟待关注的紧迫问题: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和监管问题。
精神病人伤医在近年来频繁出现,在2015年的10天里就曾发生过三起:
10月23日,广医三院住院部发生一起恶性伤医事件,28岁护士被一名59岁的住院患者持刀刺伤。警方调查显示,行凶者住院期间经常失眠,心情烦躁,出现幻觉,怀疑医务人员对其进行迫害。
10月24日,广东省惠州市中医医院菱湖院区急诊室内,18岁的实习女护士被病人砍断手筋,头皮裂伤。警方证实,行凶者与受伤护士未涉医患纠纷,此前曾有精神病史。
11月1日中午,一名女子突然闯进河南省长葛市人民医院,将一名女医生砍伤。病历调查显示,行凶者两年前曾患“精神分裂症”接受过治疗。
国家卫计委称,截至2014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到429.7万例,但以广东为例,其中仅有四成送院治疗,大量有风险,随时都可能发病、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并没有登记,散落在社会上,或者即使登记了,但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入院治疗,精神病患者伤人的事情因此时有发生。
中国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无法得到正规的治疗和监护,除了和本人与监护者缺乏认识有关,也与医患比例失调有着莫大的关系。2013年的数字,在国际精神卫生行业,平均每10万人中有4名精神科医生、13名护士;而我国是1.5名精神科医生和2.2名护士,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精神科医患比,一位精神科医生要面对840名患者。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数字,而且有可能继续恶化。
说到医生流失,很多人关注的是儿科、全科、急诊科医生流失现象,殊不知精神病科的医生同样流失严重,最大的症结在于医护人员付出的代价与其收入完全不相称。一位医生对我说:“精神科是收入最低的,而精神科专业是最难的,也是最危险的。医护人员上班时间被伤害数不胜数,连工伤都算不上。陈仲伟医生碰到的事情,我同样也碰到过,只不过运气好,现在还安稳地活着。”
陈仲伟医生的悲剧,既带有特殊性——凶手高大健壮、具有刑侦能力,尾随进入保安严密的医院宿舍,仅因25年前的一颗烤瓷牙变黄就杀人自杀;同时具有普遍性——精神病患者或偏执型人格的患者伤害医生、无差别攻击路人的事例已经越来越多,如果不在保障精神病人权益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诊治和监护,陈仲伟医生的悲剧确实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陈医生被害事件的后果,更值得每个人深思。某新闻门户对该事件的热门评论是“干得漂亮”,某些医院和医学院禁止医生和医学生前往广州英雄广场公开悼念陈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