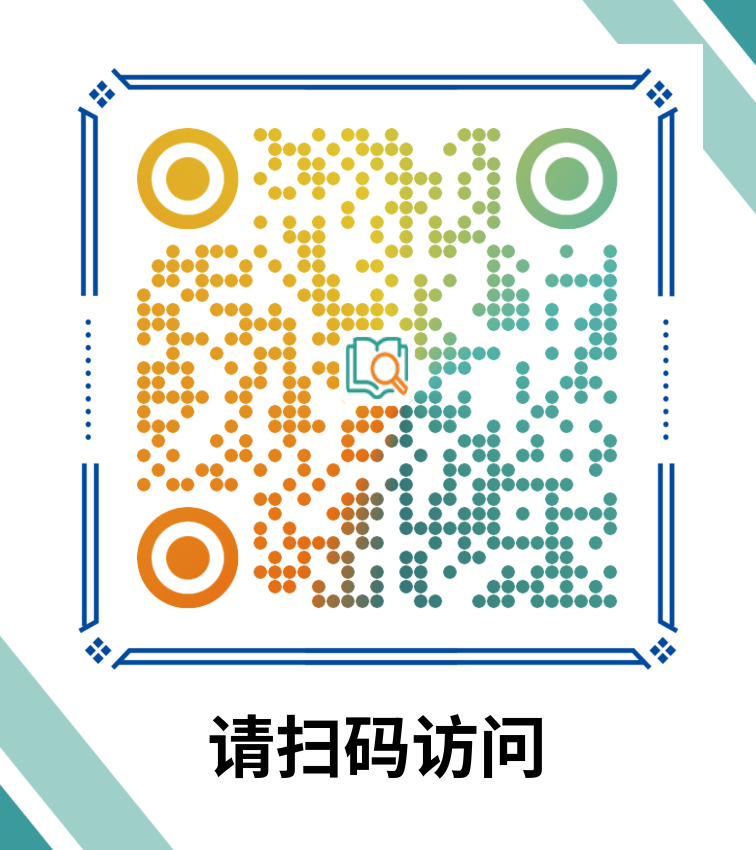那雾
时间: 11-06 来源:王孟瑜
雾存在那里很久了。当这一个小镇只有青瓦红砖时,它就在那里了;当第一个用煤的人家出现时,它就在那里了;当这一带只剩下几条田间小路时,它就在那里了。
那雾缥缈甜美,喜欢闲逛,但它依然坚守在此,白色的身躯像仙子的绫纱一样轻柔。听有的人说,有一年连续好几个月都阴沉沉的,花儿失去了灿烂的笑容,鸟儿停止了飞翔,一切就像世界末日降临一样毫无生机。但只有它轻轻来临时,人们在它的衣袖里看见了丝丝缕缕的微光,一切恍如中国水墨画一样好看。而且据说,人们还在雾里看见了神仙,漫着金光,驾着彩云。当这里还没有移民过来时,有人天天都想着它呢。
那的确是梦幻的雾。清晨,它便准时从山坡那头走到村的这头,带着青草的羞涩,泥土的朴实,溪流的宁静。使雾中难以看清邻居脸的人们,不由地深吸一口气,享一派朦胧,触一份惬意。有时候,的确,连雾也完全静止。
于是喜鹊飞来的时候,那村口的男孩就会吹起悠扬的曲子。
夜晚,雾有着自己的心事;于是那雾,那沉默的雾,暗中放下它的露珠,加大它所能带去快乐的地方,一里一里地向外。
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东西,别的东西延伸地更快,水泥地面一千里一千里地铺过来,电缆一千码一千码地架过来,商店一排一排地开张。所有原来在地面上存在的东西都被铲除。但那雾仍在清晨浓白,在新建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梦幻,更加迷人。高铁站处在山的旁边,雾把晃人眼睛的太阳光变得温和,变得比羽毛还轻,蕴含了秘密,很美,也很有诗意。
高铁像饿狼一样扑过来。有人说:这儿怎么老起雾啊?”一个保安喃喃。而且还是这么大的雾”一个旅客看着手机,一边说,手指在屏幕上疾走。在一片抱怨声和等待声中,高铁站迁移了,住在山里的大多数人家走了,只有孤零零的一户仍伫立在那里;连那喜欢吹笛的男孩,也放下笛子,沉浸在耳机里面的世界里,那一片美丽的雾不再有人欣赏。只有那雾依然在那里,依然纯洁。
啊,啊,作文雾是没有选择权的。它是阳光的使者,是雨的信使,它注定要留在这里。上帝告诉它,它在这儿诞生,也会在这消亡,它的灵魂注定留在这里。无论风力多大,无论花儿已经换过了多少千秋万代,无论它多少次的出现和消失,它都没有离开。
这天,镇长一声令下,为了搞好经济发展,迁入了几座带有高高白帽的煤电厂,从它的身体中间穿过,浓密的黑烟撕裂了它的绫纱,污了它的脸颊。空气中的浓白与浓黑搏斗着,变成了两败俱伤的灰色。一天,一月,几月,它拼死抗争着,身躯变得愈发无力,空虚;直到有一天,当黎明来临,要赶着去报信的时候,它发现它,早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它了。那雾再也没有力气反抗了,只能任凭黑烟从它的身上踩过,任凭砂砾侵蚀它的细胞,任凭它的身体里住进了另一个灵魂雾霾。在它彻底沦陷的前一天晚上,四周没有一点光亮,一切预定,一切先有默契,不再多言。父亲在煤电厂里工作的小女孩偏说,她听见了雾的悲泣;可工人没有理她,只是埋头将一铲一铲的煤丢入烈火中,升起浓浓的黑烟。
次日,一轮红日在空中冉冉升起,但却多了一份沉重与灰暗。几个清道妇,拿着扫把,缓缓地走上街头。她们望望天空,有些诧异。一个清道妇说,昨天夜里,在那雾待过的地方的鱼塘里,几百条鱼在水里上腾下跳,像是被开水烫了一般挣扎,那拍打水面的声音跟那擂鼓似的,啪啪地响,她用作证的语气说,她从没有听见那样的声音,难以相信世界上有那种强烈难言的痛苦。另一来自农村的清道妇,表现出乡间女子的独特见闻,说,那是要发生什么了。自然界的生物都是有灵性的,它们与自然共存着。一方死去,万灵具泣。这就是落幕,它们为雾哭泣。
两星期以后,人们带着厚厚的白口罩,似幽灵般地在雾霾中穿过。几乎没钱买口罩的人家,只得用粗糙的布裹在孩子身上,时不时的咳嗽一声;人们在灰色中穿梭,偶尔不小心互相擦上了,便是一阵谩骂;人们的脸无法看清,也没有任何的欢呼或悲叹。
有时在那奄奄一息的小溪上,还会有一层淡淡的,低低的雾,只不过很快就被黑烟压得无影无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