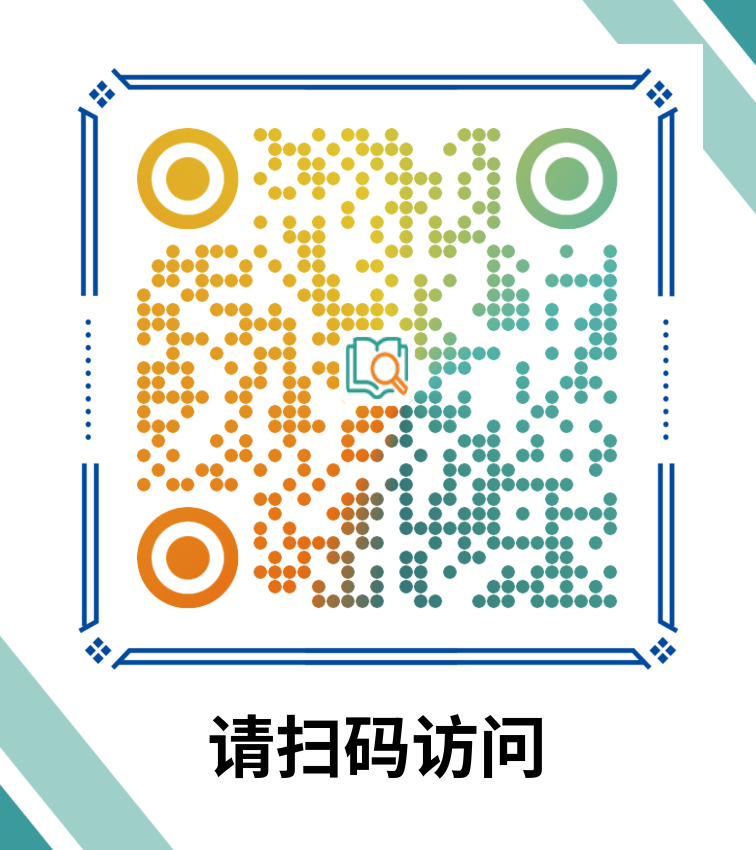那深情的凝望
时间: 11-06 来源:网络
春的恩赐是慷慨的。三月初时,老家的坡地埂圩里长遍了一种叫青”的野草儿。人们一见整簇整簇的鲜嫩,便道个清明好时节。日色渐隐,母亲摘青”回来,当晚,把青”揉进面粉里,做好青团。
第二天,母亲另备好八碗菜,父亲便把它们放入大竹箩,带着酒,扛着锄头,提着小爆竹,掂着长长的祭纸,腰里别了柴刀,一家人沿着碧野间辟出的沙路,浩浩荡荡进山扫墓了。一路上,父亲并不言语,只顾低头走路。只是不时抬眼,往阡陌尽头凝望片刻。他抿着唇,若有所思,目光却始终分寸不移那里,青山隐隐,苍穹幽蓝。
老家的丘陵四面围拢,早年驾鹤的长者安土乐之,他们,只与长着庄稼的大地亲近,只安眠在它宽大的怀抱里,忠诚地护卫着故土。
踩着刚踏新的山径,我几次偷眼觑看父亲,他只顾用锄头薅着山路两边横斜逸出的枝柯,我却觉得他的目光已经穿透山峦,穿透时光,穿回了年少当时,穿回了那似乎从未远去的岁月。
爷爷在父亲19岁时就过世了。爷爷生前是个篾匠,听说还在奉化给蒋介石做过杂役。年岁艰辛,爷爷早早离世。父亲婚后一起与奶奶住在一起,勤俭耕持,勉力为生。我九岁那年,作文奶奶积劳成疾,竟再无回春之机。父亲他们在爷爷坟旁安葬了奶奶。
老旧的石坟上枯藤绞绕,凶肆地往上攀沿,裸露的大石块不精整地垒砌着,堆成一面丘形高拱的石壁,沉沉的石台经过多年侵蚀,早已沉陷下塌。新生的春枝又爬满了高拱的墓腹。没有宽敞的台面,没有洁白的石桌,没有艳红的朱漆,也没有工整的镌字,却有一派天然的安宁。
父亲卸下随带之物,往手心吐了几口唾沫,劈开丛枝,洁扫台面,陈设酒食,堆燃祭纸,悬吊飘带,撒螺半空(取度日渐佳之意),自酌杯酒,整衣祭拜。随后,也命我们过来,告慰祖父母亡灵。不知何时,他静默地独步往山的那一边去了。
密密林木遮掩了父亲的身影,我却分明觉出他就在不远处伫立,避开我们的视线,深沉而专注地望向这边。他沉淀了岁月底色的眼睛,仿佛展开了这几十年的生活画卷。他的目光,仿佛描绘了这些年务工务农的辛劳,仿佛在向已故的双亲诉说这这个家庭的建设与兴盛,未来与发展。他的凝望中,有无可挽回的哀切与酸辛,也有不能尽数的满足与欣慰。
祭拜完,我们信步拾级。登山而渐高,父亲仍是端凝地望着。杜鹃汹涌,泼泼洒洒,故人当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