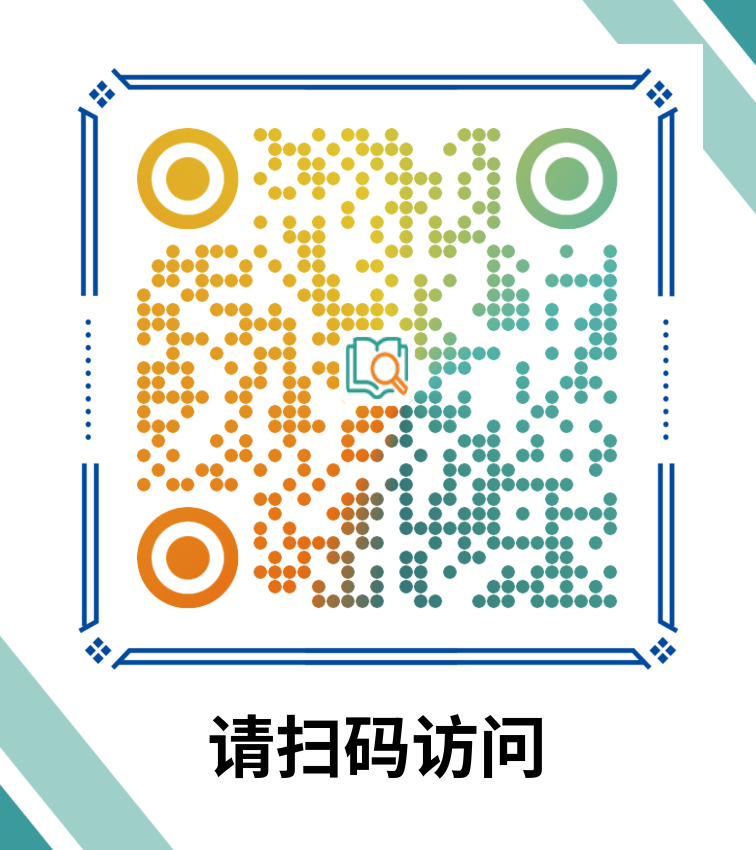讲标人
基本解释
“讲标人”是历史上广东“主僮”(原居于广东的古越族的一支)的一部分,其不同于从广西迁来的“客僮”,这些“主僮”后来又融合了部分汉族人口,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讲标人”这个独特的人类群体;而伴随着民族的融合及文化接触、交往等等,终于发展出现代“讲标人”的文化,它是各族文化交融的结果,其中“标语”本身就是证明之一。
详细解释
分布范围及人口
“讲标人”又称“标话”集团,主要居住在广东省部的怀集、封开两县。居住于怀集的“讲标人”较多,约15万人,集中在该县南部的诗洞、永固、桥头、大岗等乡镇。居于封开的“讲标人”人口较少,约有7000多人,集中在县北长安镇一带。以上怀集、封开两县的几个乡镇在地理上构成一个以党山山地为中心的独特区域,这也就是“讲标人”的主要活动区域。
“标话”
“讲标人”因操一种属于壮侗语族与壮语比较接近的语言“标话”而得名。经过语言学家的研究,“标语”被认为是一种混合语,与汉语有较大的差别,可以归入壮侗语族中,但其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一种语,或者说是否可以独立成语,至今未有定论。
“讲标人”不承认自己是汉族
“讲标人”一直自以为与汉族不一样。解放初土改时填报民族成分,怀集有不少农民填报为壮族,但没获批准。以后有人参军参干时,亦填报为壮族,同样不获批准。而集体性向当地政府(怀集县政府)提出要求解决族属问题的行动分别发生在1956年和1982——1993年。为此,怀集县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研究,由该县政府向广东省府办公厅、省民委等部门报请识别该县“讲标人”的族属问题,并得到上级的重视。到1986年夏天,广东省民委组织了一个有12人参加的民族识别调查小组,赴“讲标人”人口集中的怀集县南部的诗洞、永固、桥头、大岗等乡进行调查研究,嗣后写出综合研究报告,由省政府提交给国家民委,要求确认“讲标人”的壮族成分。不过这一意见最后未被国家民委所接受。
虽然解决“讲标人”族属问题的工作最后没有取得成功,但当时民族调查识别工作带给广东民族学界的影响却不可低估。
研究结果
首先,当年参加调查工作小组的一些学者认识到“讲标人”的研究价值,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分别完成若干篇研究论文,或者使用“讲标人”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资料来探讨相关问题,从而拓宽了广东民族学研究的领域。这些学者如广东民族研究所的练铭志研究员、广东民族学院(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前身)的姜永兴研究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客观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均如研究员,等等。其次,省内一些学者受到民族调查识别工作的影响,关注“讲标人”,并利用“讲标人”的社会文化资料进行研究,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宋长栋教授。再者,还引起了一些年轻学者对“讲标人”语言社会历史文化的兴趣,陆续进行调查研究,如颜冰受当年“讲标人”民族识别研究的鼓舞,在1988年就以封开县“讲标人”的语言研究完成了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到2001年夏天,我们又一起对封开县长安镇的“讲标人”进行田野人类学的调查研究。
上述学者的相关研究结果,均持有下述的观点,即“标语”有别于汉语中的任何一种方言;“讲标人”不同于汉族;“讲标人”的文化是历史上南方百越民族与南迁汉人,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交往从而产生文化交融的一种结果。
封开“讲标人”深入调查报告
封开“讲标人”集中居住在县北长安镇。根据调查统计,长安镇共有农村户口的“讲标人”6600余人,约占全镇人口37000人的18%。至于已经把户口从农村中迁移到城镇或者外地的“讲标人”的人口则无法进行统计,据当地政府估计约有数百人,新出版的《封开县志》介绍“标语”时认为封开“讲标人”有7217人,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真实状况的。
当地还有部分人口,原来是讲“标话”的,因种种原因不再讲“标语”,这些人口并已被当地“讲标人”视为异类,列入“不讲标”类别。如长安行政村内的楼下墰自然村(林姓),宝山行政村内的下罗柴自然村部分人口(梁姓)、梅花自然村(梁姓)、罗待自然村(褥姓)等等聚落的人口,总数约百人,已不再讲“标语”,不再被当地社会承认人“讲标人”。但是这些人与各自同一姓氏的“讲标人”又保持着密切的同宗关系,仍在一起祭祖。我们在统计“讲标人”人口的时候,撇除开了这些已被看成是“讲开建话的”人口(开建话为粤语的一支,因历史上的开建县而得名)。
近七千人口的“讲标人”主要居住在长安镇长安、宝山、东山三个行政村及下罗境长安墟里,约有40余个自然聚落。这些聚落分别是:长安行政村的庙后、大街、墰榕、上罗境、大巷街、万荣寨、长岗、上宅、长远、银铺、城巷、帝两(又分为军荣、墰凤、石坎、大松)、帝木、上墰寺、更楼(长群)、罗仇、凤寨、安成、罗迈、大园、大棚、水涝、七座、墰田、长安旧墟;宝山行政村的下罗柴、文林、上东、上西、桥头、宿水、范两;东山行政村的寨东、寨下、李户、李宅、白屋、上屋、中南、南屋、花门楼、长江;长安镇府所在地长安墟,等等。这四十多个自然聚落(聚居地)散布在长安墟周围,距镇府最远的村落亦只在三公里左右。
“讲标人”的主要姓氏是褥、梁、仇、卢、陈、林、苏、李、袁等,个别小姓如唐、叶、朱等人口很少,往往只有几个人或者十余人。一般大姓者曾建有宗祠,“文革”时被拆,现在已见不到旧的祠堂。现在能见到的只是宝山梁氏在原址上重建的梁氏宗祠,其亦是刚建起而尚未装修完毕。其他大姓有的有准备重修宗祠的计划,有的则对此并无任何准备。一般而言是经济上的原因,使他们尚无力顾及此事。
部分“讲标人”过去亦曾编有族谱,现今均已散失,原因是解放前当地有个土匪头子,常抢掠烧杀,特别把各姓氏(村落)的炮楼视为眼中钉,常在夜间偷袭炮楼并以火焚之。而各姓的族谱一般是存放在炮楼之上的,故难以幸免。极个别幸存下来的族谱,到“四清”和“文革”时也逃不过厄运,被毁于一炬。这样,今天人们就无法把自己历代的来龙去脉及诸先祖的情况讲清楚。不过,与重修宗祠行动相一致的是,人们正设法重修族谱。
封开“讲标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种植水稻、薯类、豆类、玉米等以及经济作物瓜菜、莲藕之类,产量较高,但因价格偏低,效益不好。养殖业为养猪、牛、鸡、鸭、鱼、狗等等。在村寨里房前屋后种有龙眼、黄皮、芭蕉等果树。由于东部山地(即党山西麓)多石,居于长安行政村、东山行政村的“讲标人”只获得少量旱地,宝山行政村的情况好些,那里有些小丘陵山坡地可资利用。总体而言,“讲标人”的经济仍然属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商品农业经济的成分较少,同时在当地从事工商服务业的“讲标人”亦很有限。因为外来人口少,封开北部一带工商业不发达,内需不足,甚至连蔬菜、普通肉类等基本生活品的销售量都极为有限,所以当地“讲标人”在传统农业之外较难获得收益。
但是封开“讲标人”又并非过着一种传统式的农民生活,事实上他们难以享受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共享天伦的田园生活。这些年来,外面的世界把年轻的男男女女吸引去了,留在村落内的以老人、中年妇女、小孩为主,农忙季节才能看到几个回家帮干农活的青壮年,但即使是农忙季节,田野中干活的人仍然以妇女、中小学生为主。这就充分说明“讲标人”社会已受到外部世界的强烈冲击。再看看村寨内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水泥钢筋楼房,可以看出现代化正在影响着“讲标人”和他们的社会文化。
封开“讲标人”中的文化交融现象 封开“讲标人”的人口来自于百越民族及部分南迁汉族,正是各民族间的相互混血以及文化交往、文化交融、文化认同,形成了今天的“讲标人”。因此,在“讲标人”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具有明显的文化交融特点。“讲标人”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在“讲标人”社会中,文化交融现象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标语”本身是各种语言相互融汇的结果 语言学研究表明,“标话”词汇中约有一半左右是借用汉语粤方言的,这表明“标语”与汉语之间的联系。另据研究,“标语”的基本词汇,与任何一种汉语之比较都相差甚远,而在语法上也有与汉语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如修饰词放在中心词的后面,如“眼泪”说成“水眼”、“青草”说成“草青”、“糯米”说成“米糯”。这说明“标话”既有汉语成分,又有非汉语成分。据当年对怀集“标语”的调查发现,“标语”中有60%左右的基本词汇不属汉语词汇,而与壮语南部方言相同或者近似(占34%),或者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占26%)。这一研究对封开“标话”的分析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可以证明,“标话”是各种语言相互交往而产生的结果,是文化交融的结果之一。
而从地名学上来看,封开“讲标人”集中的长安地区的地名中,以“罗”字开头的有不少,如罗境、罗迈、罗仇、罗柴、罗待等等。还有以“墰”字开头的地名,如墰田、墰寺、墰榕、墰迈、墰亭、墰这等等,实为壮侗语地名。这就说明封开“讲标人”生活的地区,是古代壮侗语族某个族群(可能是西瓯)生活过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在“讲标人”与壮侗语族诸族群间建立起某种文化联系。
2. “讲标人”的宗族组织及其活动体现出文化交融的特点
封开“讲标人”的宗族组织,有两个主要的表现特征:
第一个是,坚持汉族传统宗族制度的基本规则,这主要表现在重视血缘关系方面。“讲标人”同姓不婚,但若是同姓而不同属于一个宗族则可以通婚,也可以与非“讲标人”中的同姓结婚。这表示其主要是从血缘上来考虑婚配对象的。另外,他们排斥无共同血缘关系者,如对拖油瓶仔,允许其随姓,允许其在本姓族范围内耕种土地,但不允许其成年后(18岁之后)仍居住在本姓村寨内或在村寨内建房子,而必须在村寨外面另辟地自立门户。自然,拖油瓶仔及其后代子孙是不允许参拜本姓宗祠的。
此外,若是异姓养子,虽曾随姓,同样爱到轻视甚至欺负,被限制从事某种活动(如在村寨内建房子,祭拜宗祠等),因而养子在娶妻成家并人丁增多时,他和他的子孙都会考虑归宗问题,即回到与自己同一血缘关系的宗族。事实上后者亦是非常欢迎这部分子弟回归的。因而在“讲标人”这里,常会出现某个姓氏的某个宗支集体改姓的事,而且又常伴随搬迁或另辟村落。比如原来更楼有部分卢姓人口,集体性地搬迁到今长群村地建屋成村,并成功恢复为林姓,即其同一血缘祖先的姓氏。这是因为这部分人口原来的祖先来自墰寺林姓,被一卢姓夫妻收为养子并随父姓卢,但其后代总被卢氏排斥,故只好找机会脱离卢氏另辟新村,这件事说明了“讲标人”是多么重视血缘关系。然而,另有一件事又说明了“讲标人”虽重视同一血缘关系,但对已改为他姓的有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不管出自何种原因,亦不准其参拜宗祠,修建宗祠时亦不接受其捐助。这又反映“讲标人”还讲究血缘之外的姓氏这种外在符号的象征意义。比如历史上罗柴有一个梁姓男孩,父母双亡后跟罗境的姑父母长大,并随姑父姓陈,其后代至今约有几十人,在罗境寨外辟地自立成村。因其始终不改换姓氏为梁,而被罗柴的同血缘关系者视为异类,自然无法参拜梁氏宗祠。而同时他们又被罗境陈氏视为异类,被称为“假陈”、“野陈”,亦不准参加陈姓的祭祖活动。因而这部分真正的梁氏后代的陈姓人左右为难,哪儿都不是人。为此他们曾求助于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罗柴梁氏,回答是:“只要改为梁姓便可以重入宗祠,参拜祖先”。罗境村中这部分“假陈真梁”人口的遭遇,最明显地说明了封开“讲标人”既重视同一血缘关系,又讲究姓氏这种外在符号的象征意义。